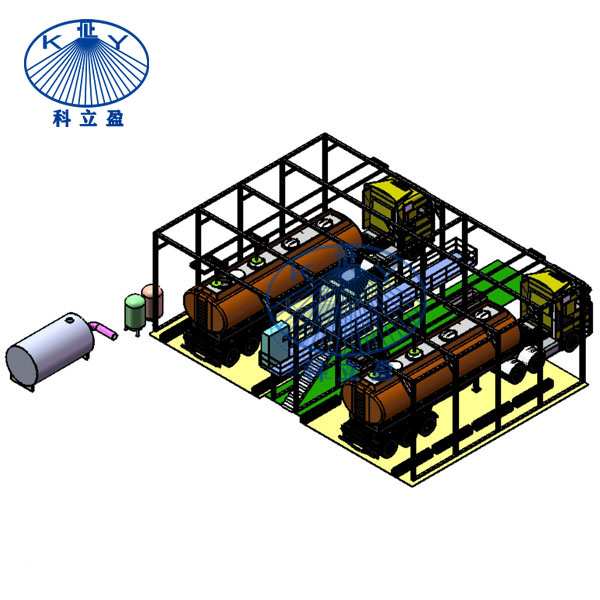讨论社保与福利有一个好的分析框架很重要
时间: 2025-08-21 18:36:02 | 作者: 清洗头/洗罐器
提示:点击图片可以放大最近关于社保的讨论还没停,我也看到了一些有意思的讨论文章。借着这个机会,我们刚好可以来讲一本社会福利领域的经典著作,戈斯塔艾斯平-安德森的《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我想,政治学,社会学与研究社保方向的读者朋友对这本书是不陌生的。如果大家对这本书内容有什么看法或心得,也欢迎在评论区讨论补充。
首先是去商品化,这一维度关注社会政策在多大程度上能让人们的生活水平摆脱对市场的依赖。去商品化的程度,具体通过福利的资格条件、收入替代率以及覆盖范围等方面来衡量。例如,福利获取要不要严格的工作经历或经济情况审查,福利水平能否接近正常收入,以及福利覆盖人群的广泛程度等,都直接影响着去商品化的程度。
其次是社会分层,探讨福利国家如何塑造社会阶层结构。福利政策并非仅仅是对现有不平等的修正,它自身就是一种分层机制,会影响社会中的地位差异和群体团结。比如,不同的福利分配的方法可能会强化现有的阶级或身份差异,也可能促进社会平等,或是造成新的社会二元分化。
再者是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尤其聚焦于两者在福利提供中的互动。以养老金为例,分析公共与私人养老金的构成比例及相互作用。研究之后发现,国家在私人福利市场的形成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如通过税收优惠等政策影响私人养老金的发展,而私人福利的状况也会反过来影响公共福利的设计和实施,两者共同构成了福利体系的整体框架。
工人阶级与左翼政治的力量大小尤为关键,左翼政党在议会和内阁中的席位占比等因素,与福利政策的走向紧密关联,而当工人阶级的组织力量较强时往往推动更全面的社会福利。
天主教与基督教政党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它们所秉持的社会理念会塑造福利政策的倾向,尤其在强调家庭和传统社会结构的福利安排中体现明显。
历史上的专制主义遗产同样有影响,那些经历过较强且持久专制统治、较晚落实普选权的国家,其福利体制往往带有更多等级化和国家主导的特征。
在福利体制方面,经济和人口因素的影响有限。经济发展水平和增速会影响福利支出的总量,不过对福利体制的类型区分影响有限;人口老龄化会推高养老金等福利支出,但也并非决定福利体制性质的核心因素。这一些因素相互交织,共同塑造了不同福利体制的面貌。
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保守主义的福利体制。保守主义福利体制的代表国家包括奥地利、比利时、法国、德国、意大利等。
保守主义福利体制核心特征,是其维护传统社会秩序,巩固等级差异的倾向。这种体制的根源与保守主义思想、天主教教义及专制主义历史遗产紧密相连,其设计初衷并非追求平等,而是通过福利政策巩固既有的社会分层,避免资本主义带来的阶级对抗与社会碎片化。
从历史来看,保守主义福利体制的早期形态可见于俾斯麦时期的德国等国家,当时的改革者将福利视为维系权威的工具通过提供社会保险,将工人忠诚绑定于君主制或中央政权,同时刻意保留不同职业、身份群体的福利差异,强化“各安其位”的社会秩序。天主教教义中的“辅助性原则”也深刻影响其走向,即国家仅在家庭、社区等传统单元无力保障时才介入,这使得家庭在福利供给中承担核心角色,而公共服务如托育等往往发展滞后。
在制度特征上,保守主义福利体制呈现出明显的“社团主义”和“国家主义”色彩。社团主义体现为福利计划按职业、身份分割,不同群体(如工人、公务员、教师)享有独立的保险体系,规则、福利水平各不相同,文档中多个方面数据显示,德国、奥地利等国存在大量职业隔离的养老金计划,强化了阶层界限。国家主义则表现为对公务员等特定群体的特殊福利倾斜,如奥地利、法国的公务员养老金支出占GDP比例明显高于其他群体,以此维护国家权威与官僚体系的稳定。
这种体制的去商品化程度中等,福利资格多与就业记录、缴费年限挂钩。例如,德国的养老金依赖长期贡献,虽能提供一定保障,却难以让人们完全摆脱市场依赖。在社会分层上,它通过维系身份差异巩固秩序既避免了市场带来的原子化,又防止平等主义原则对传统权威的冲击,但也导致福利的再分配效应微弱,阶层差距难以缩小。
其形成与政治力量紧密关联,天主教政党的影响力和专制主义历史遗产是关键。多个方面数据显示,天主教政党席位占比高、专制统治历史悠远长久的国家,更易形成此类体制,它们通过福利政策将传统社会结构制度化,成为保守主义福利体制的核心支撑。
接下来是自由主义福利体制。自由主义福利体制的代表国家有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瑞士等。
自由主义福利体制的特点,是其对市场机制的依赖,以及对限制政府干预的坚持。这种体制的核心逻辑是,福利供给应主要由市场和个人责任承担,国家仅在市场失灵时提供最低限度的保障,避免过度干预破坏竞争和个人自由。
从历史根源来看,自由主义福利体制与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紧密相关,强调个人自足、契约自由和最小国家。早期的济贫法是其雏形,通过严格的家计调查和低水平救济,迫使人们依赖市场而非国家,比如19世纪英国的济贫制度,旨在防止福利依赖削弱工作激励。这种思路延续至今,形成了以社会救助为核心、私人福利为主导的体系。
在制度特征上,自由主义福利体制的去商品化程度较低。福利资格多与经济情况挂钩,即家计调查,且福利水平通常仅能维持基本生存,如美国的社会救助项目,受益群体主要是低收入者,且常伴随社会羞耻(social stigma)。同时,私人福利扮演重要角色,个人和企业通过商业保险、职业福利等满足更高需求,文档多个方面数据显示,美国私人养老金占总养老金支出的17.1%,私人健康支出占比达57%,远高于其他体制。
社会分层方面,自由主义福利体制容易形成双重结构:低收入群体依赖国家的有限救助,中高收入群体则通过市场获得更充足的福利,导致福利获取与经济地位直接挂钩,强化了社会分化。这种分层并非偶然,而是制度设计的结果通过税收优惠鼓励私人福利,实则让有能力者获得更多保障,而难以企及。
政治影响也很重要,自由主义体制下,工人阶级与左翼政党往往力量较弱,难以推动普惠性福利改革,而保守主义和自由市场理念主导政策走向。经济因素中,较高的人均GDP与私人福利的发达相关,但这并非福利体制的核心决定因素,其本质仍是对市场主导和个人责任的坚持,即便在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国家,这种体制也会因政治理念差异而保持独特性。
接下来是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体制。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体制以北欧国家为代表,如瑞典、挪威、丹麦等。
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体制的核心特征,是其追求普遍主义和高度去商品化,强调通过福利政策实现社会平等与团结。这种体制的形成与社会的长期执政紧密关联,其设计初衷是打破市场对我们正常的生活的绝对控制,让所有公民无论职业、收入或身份,都能享有平等的社会权利。
从制度特征来看,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体制的去商品化程度最高。福利覆盖全民,且资格条件宽松,不依赖严格的家计调查或长期缴费记录,比如瑞典的养老金和疾病福利,不仅覆盖范围广,而且替代率高,能让受益者维持接近正常工作时的生活水平。文档中的多个方面数据显示,1980年瑞典的综合去商品化得分高达39.1,远高于其他几个国家,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公民对市场的依赖程度大幅降低。
在社会分层方面,这种体制致力于缩小阶层差异,通过普惠性福利政策促进社会 团结。福利项目不按职业或身份分割,而是面向所有公民,比如全民统一的养老金体系和普遍的儿童津贴,减少了因福利获取差异导致的社会分化。同时,其福利水平向中高收入群体的标准看齐,避免了福利仅能满足基本需求而形成的二元结构,让工人阶级也能享受到与中产阶级相当的保障,从而巩固了广泛的政治支持。
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上,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体制以公共福利为主导。社会民主主义体制往往通过高税收支撑全面的社会服务,同时限制私人福利的作用,防止市场力量破坏福利的普遍性。例如,瑞典的公共养老金占比高达85.5%,私人养老金仅占4.4%,确保福利分配不受市场不平等的过度影响。
此外,这种体制注重将福利与就业结合,通过扩大公共服务领域的就业(如教育、医疗、养老服务)来实现充分就业,尤其推动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文档中提到瑞典公共就业占比达33%,女性就业率明显高于其他体制,既保障了经济活力,又强化了福利体制的可持续性。其背后的政治逻辑是,通过广泛的社会权利分配,培育跨阶层的团结,让福利成为全民共享的公共产品,而非特定群体的特权。
在政治方面,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体制基本都出现在那些工人阶级政治力量较强的国家。具体而言,就是社会在议会和内阁中拥有长且显著期影响力,工会组织统一且强大,并且能形成容纳农民与新中产阶级的广泛阶级联盟。
安德森也基于他的分析框架对西方各国福利体系的后续发展做出了一些展望。在他看来,未来福利制度如何变迁,阶级问题是关键。
反对福利,是因为社会负担大吗?其实并不是。福利国家的紧缩或衰退风险并非由社会支出负担过重决定,反而那些福利支出最高的国家,反福利情绪往往最弱,而支出较低的国家反而更易出现反对声浪。
福利制度的核心在于其阶级基础:社会民主主义与保守主义福利制度下,因中产阶级能从中受益,容易形成稳固的支持联盟,从而更能抵御反福利压力。相反,自由型福利国家依赖弱势社会阶层的支持,这类群体在政治上影响力有限,其福利体制更易面临削减压力。
作者认为,福利制度的未来走向,本质上取决于其建立时形成的阶级联盟能否持续:那些成功将中产阶级纳入福利体系、让全民共享福利成果的体制,更可能维持稳定;而仅服务于特定弱势阶层的体制,则更易在政治变迁中出现收缩。这种预期强调,福利制度的生命力不在于支出规模,而在于其能否构建广泛的社会共识和跨阶级支持。
最后总结一下文章框架。作者在书中提出的分析框架围绕福利资本主义的三种体制展开,核心分析维度包括去商品化、社会分层以及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去商品化衡量社会政策使人们摆脱市场依赖的程度,社会分层关注福利制度对社会阶层结构的塑造,国家与市场关系则聚焦两者在福利供给中的互动,如养老金的公私混合模式。
影响这些体制形成的重要的条件是政治力量,其中工人阶级动员强度与社会民主主义体制关联紧密,天主教政党影响力和专制主义遗产对保守主义体制作用显著,而自由主义体制则往往在那些左翼力量较弱,主流政策导向高度亲市场的国家。经济与人口因素虽有作用,但更多影响福利支出规模而非福利体制类型。
当然要说明的是,文中提到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三种福利体制,更多的是一种“理想类型”,帮我们理解福利体制的不同倾向。所以我们要注意到,每一个具体国家的经验往往都很复杂,即便是文内提到的各体制代表国家,也难以轻易随便套进任何一个体制。另外,艾斯平-安德森的研究大多分布在在西方社会,因此在分析阶级与政治问题时,会以欧洲的历史经验为主。我国与广大亚非拉国家的情况可能更复杂。
不过即便如此,我想在一个更高的抽象层次上,这本书可能还是能给大家思考我国当下社会保障机制提供一些启发。
“先锋队”还是“总管家”?——论为何只能为人民服务,而绝不能为资本家服务
没有毛主席的“因”,哪来“改革开放”的“果”?——论“前三十年”为“后四十年”奠定的历史总前提
《98-08 大抢劫:国有资产私有化实录——血色账本里,每一页都写着名字》
《98-08 大抢劫:国有资产私有化实录——血色账本里,每一页都写着名字》
《98-08 大抢劫:国有资产私有化实录——血色账本里,每一页都写着名字》

 English
English